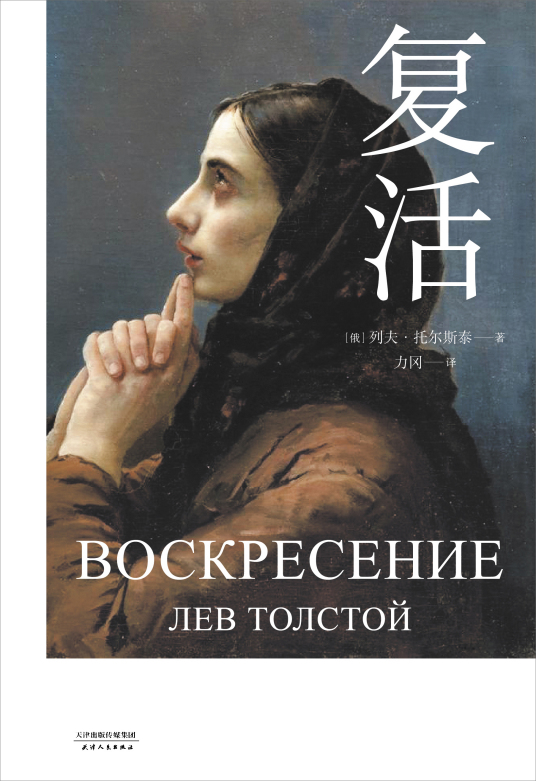月亮和六便士读后感1200字
曾经有人问我:“还记得你年少时的梦想吗?你可曾为之奋不顾身?”我怔住了。梦想——这个词是如此的遥远,它像一枚遗落多年的书签,忽然从时光的夹页中滑落。为了生活,我们都像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为柴米油盐奔走,在一个安全地带碌碌而为。谈论梦想,是不是有点奢侈?
我们都曾拥有滚烫的梦想,像十八岁的夏天,不知疲倦,不信边界。可不知从何时起,它被悄悄藏进了生活的暗格,已经被逐渐遗忘。我们慌慌张张,为了责任,为了那几两碎银,每天奔波忙碌,在固定的轨道上重复着相似的每一天。“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北岛的诗句便是最好的写照。
直到我遇见《月亮和六便士》。
“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毛姆笔下的“月亮”与“六便士”,成为一个永恒的隐喻。月亮,是那遥不可及却始终皎洁的理想;六便士,则是我们俯身即拾的现实。而书中主角思特里克兰德,一个中年证券经纪人,某天突然抛下一切去学画,甘愿承受贫穷、病痛与世人的不解,最终在南太平洋的岛屿上将生命燃烧成画布上的永恒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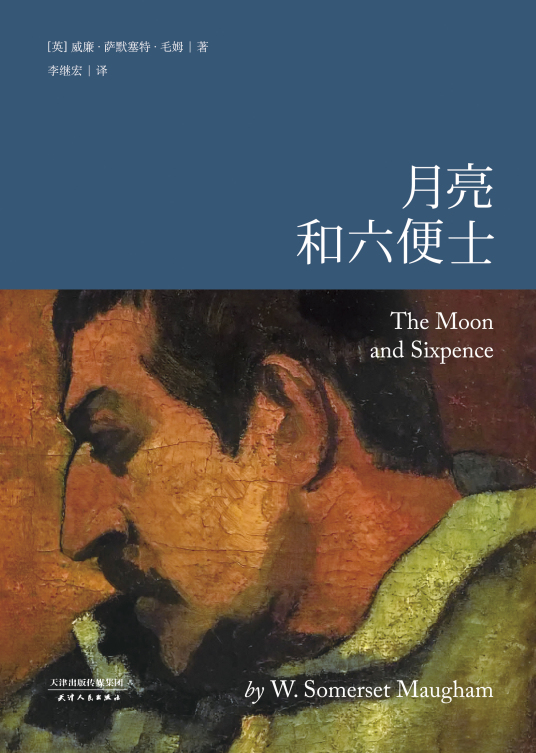
他或许是世俗意义上的“疯子”与“自私者”,但他对内心召唤的绝对忠诚,却像一记重锤,击醒了我沉睡的某一部分。
我曾经也是一个有梦的人。中学时躲在被窝里,听着收音机,那时特别想当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想当一名摄影师,背着单反相机走遍天下,用镜头定格时光,不出远门的话在家门口拍拍花鸟也可以,光影之间尽显艺术之美;幻想着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来一场穿越欧洲的长途旅行。可后来,收音机不知塞进了哪个角落,古筝也在房间里落满了灰尘,那本欧洲地图也早已脱页,字迹模糊。那些热烈的日子,仿佛从未发生。
直到前段日子,我在整理旧物时翻出一本小册子,纸页泛黄,上面是歪歪扭扭的字迹,写满对远方的想象。继续往后翻,竟然是多年前西藏之旅的点滴记录,彼时的我是一个背包客,勇闯318国道,记录下经过的每一个地名:康定、理塘、芒康……在路上遇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朋友,或许连朋友都算不上,他们只是在小本子上留下了美好的祝福,有藏语也有英文,不知他们是否还记得我这个过客?那一刻,我忽然眼眶发热——不是感伤逝去的时光,而是那些闪亮的日子让我惊醒:我是什么时候,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了?
毛姆借斯特里克兰德之口诘问:“做自己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是糟蹋自己吗?”
这句话如月光照进现实。我们未必要像他那样抛弃所有,但我们依然可以在六便士的世界里,为心中的月亮留一扇窗。
于是,我开始在生活的缝隙里重新寻找光。周末不再只顾埋头琐事,而是留出半天,读一本“无用”的书,笨拙地写下几行读后的感受。甚至安静地听一场雨,养几尾悠然自得的金鱼,种几盆喜欢的植物,不管它开不开花。有时坐在蓝天之下,看看云,发发呆,放空自己,也是很美好的时光。或者独自一人,背上简单的行囊,去爬一座山,看一座城,吃一顿美食。我不再把自己完全交给忙碌,而是试着在现实的土壤中,种下一颗属于精神的种子。
人到中年才明白,人这一生,哪有什么标准答案,大部分人都是用尽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所以,我们最要紧的不是取悦他人,而是丰盈自己。也许我们无法逃离六便士的世界,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偶尔抬头,让月光洒在脸上。凡心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
只要你愿意,那月亮,始终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