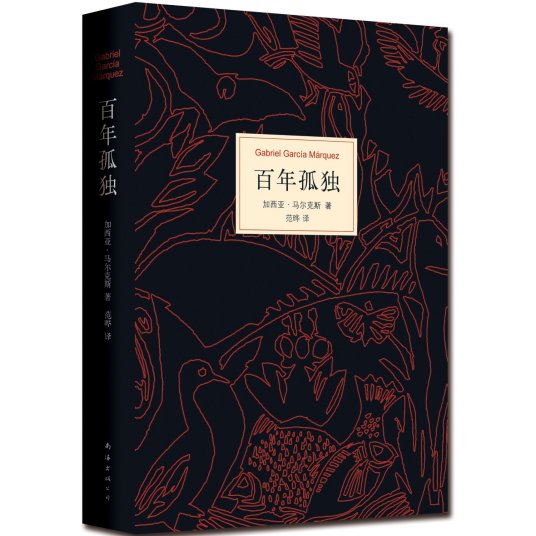《我与地坛》读后感1000字
《我与地坛》读后感1000字1
若硬要用一个词概括《我与地坛》的写作风格,“轻幽”二字大抵最为贴切。“轻”,源于史铁生惯以联想与想象为笔,在扎实的叙事与描写之上,捕捉万物的灵性与生机——虚实交织间,文字仿佛卸下了重负,只剩通透的轻盈。而“幽”字,则藏在他典雅的用词里,又显在锋锐的语句中,恰似鬼魅般清绝,带着一种含蓄却深刻的力量。他对文字的掌控始终松弛自在,字句间满是沉浸的质感,循着字里行间望去,便能触到他精神世界的一角,那片辽阔又寂寥的虚无旷野。正如他在文中常说的:人生本无意义,而荒诞,反倒为生命赋形。
史铁生的一生,与地坛之间始终牵系着一种近乎灵魂层面的羁绊。早年间他曾说,因为地坛,竟开始感恩自己颠簸的命运;可一想到将来要与这片园子分离,又涌起满心矛盾的思念。他在园子里缓缓拨动轮椅轮盘,碾过一轮又一轮春夏秋冬,从青丝染鬓,到暮年垂首。目送着一重又一重人路过、停留、远去,也总在心里琢磨:在地坛遇见的这些人,他们的行为背后藏着怎样的缘由?又藏着怎样的生命哲思?
那对从壮年相伴到老年的夫妻,始终恩爱如初;还有那个弱智却模样漂亮的女孩,好与坏在她身上奇妙地融为一体。史铁生大抵是想说,若这世界只偏向某一端的极致,便会沦为一潭没有波澜的死水。苦难于人类文明而言,从来都是无法回避的必然,可真正的救赎之道,又在何方?并非人人都有般若的悟性引路,能寻着涅槃的方向。
还有那个总被命运捉弄的长跑小伙子,他总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质,而整个人生,不过是一场看不清尽头的未知阴谋,荒诞得让人无力。“人质报复阴谋最彻底的办法,是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便能挣脱束缚,获得所谓的“自由”。可这又谈何容易?史铁生在文中反复写道:“人真正的名字是欲望。”可若将欲望消灭,生命似乎也随之消逝。他曾细细叩问地坛的“园神”,只得到一句低语:“这是你的罪孽与福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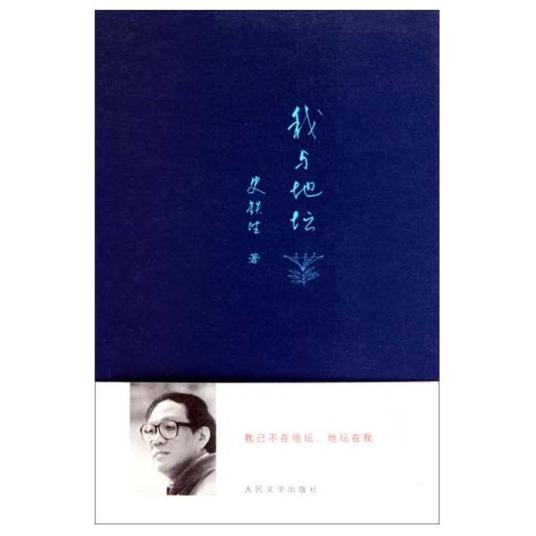
在地坛最后的那段时光里,他似乎恍惚看见两个自己:一个正缓缓走下山,另一个却抱着玩具、以孩童的模样,一步步爬上山。就像他在文中写过的那样,他再一次,也是无数次地,他重新回到了“零度”。
“零度”,是史铁生离开地坛后所写下的思念。想念地坛,想念它的宁静:一个惶惑的灵魂,不经意间走回生命最初的起点。他以“零度”慰藉思念,也借此表达一种难以言说的回望。人活于世,总在无数事件与选择间迷失,忘了为何出发。迷茫辗转之间,电光石火般蓦然笑对荒诞,便是又一次回归“零度”。这与他的两个世界观不谋而合:生命本无意义,而对意义的追问本身即是荒诞。或许可以说,唯有“当下”才是意义本身。意识到这一点,便是第二次生命的开始。
正如他所说:“想念地坛,就是不断地回望零度。”而那句穿透岁月的“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或许也藏着这样一层深意:“自遇见地坛那天起,我便在无数次回望里,一次次回到了荒诞生命的‘零度’。”
《我与地坛》读后感1000字2
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离合即循环,忧喜迭相攻。人活于世,岂有一帆风顺之理?所经之事,不如意者,十有八九。未经磨难的苍鹰常为幼雏,些许霹雳便能喝退它的航行;未经风雨的花朵常是花骨,些许寒霜便能摧毁它的枝芽。拥有满腔热情与满身力气的青年,若是遭遇了巨大的苦难,命运的不公,将会如何?答案在这本《我与地坛》之中。
作者史铁生因大病痛失双腿后,在母亲的引导下,选择将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之中,以创作热情延续自己生命的火苗。《我与地坛》记录了病愈初期的史铁生在地坛里的所听、所闻、所见、所感。一天,一年,数年,园子中的声音,园子中的气味,园子中的景物,园子中的心绪,随着记忆,伴着文字,冲上眼前。其中蕴含着作者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大彻大悟的哲思,是无声的呐喊,也是动人的赞歌。
就像盲人对声音格外敏感那样,史铁生因为不能走动,便坐在轮椅上,静静地欣赏这座美丽的地坛,想在一个寂静的世界中躲避另一个悲惨的世界。蝉声,鸟声,人声在书中被描写得响亮,园子的四角被描绘得清晰。古殿檐头的风铃,爬满青苔的石阶,独独徘徊的雨燕,无不映着他的足迹。他又写,园子的昼夜,园子的四季,将其比作时间、乐器、声响、心绪、艺术等。华丽的想象力让其像老友般向读者讲述他最亲近的兄弟——地坛。那描述令人感到亲和并好奇,那陈述使人仿佛真的看见,作者笔下,那个最长情的地坛。
史铁生并非一开始就深爱着地坛,最初,受命运折磨的他感到深深的痛苦,他想寻死以求解脱,却碰见了一位深爱儿子的母亲。即使史铁生对母亲的态度恶劣,对其的所作所为有抱怨,责怪和愤怒,但母亲总在他的身旁。即使史铁生对人生感到麻木,依然有一道光照向他,并为他开辟了写作的路。他坐在地坛中回忆着,从他无比怀念的母亲到后来形形色色的人们——美丽但智障的女孩、辛苦但不幸的运动员、平凡但幸福的夫妻……作者的笔写出了它们的苦难和时代的背影,并借由自己进行了思考:所有人都会遭到困难,受了挫折,有了参差,才有了差异。才有了好与坏,美与丑的对比。才有了智者与愚者,善人与恶人,苦难与幸福。这思考解答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问题,是生,还是死。一位不被命运眷顾者,对于人生的态度很简单,只是坦然面对,在苦难中洗涤自己,在悲痛中修补自己,坚信着“上帝爱我”,而怀抱快乐然后活下去。人是受够了痛苦,而不是受够了活着。因为每个人都想在生命当中获得一种意义,是“英雄主义,热爱生活”或是“生存毁灭,我尽接受”。他告诉读者:既无法改变这惨淡的命运,那就向命运反击——从好好活开始,在这苦难遍地的世界,作者用它优美的文笔讲述了一个温柔的道理。
故事的最终,满腔热情与满身力气的青年拿起了笔,将笔尖对准了不公的命运,以苦难为墨,以灵魂为诗,在死亡的边界上,书写出反击命运的诗篇。若死亡终将来临,那么在仅有的时光中,请载歌载舞地活着。人生是罪孽,也是福祉。苦难既然存在,那么美好也一定存在,不妨简单些,去直面你的命运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