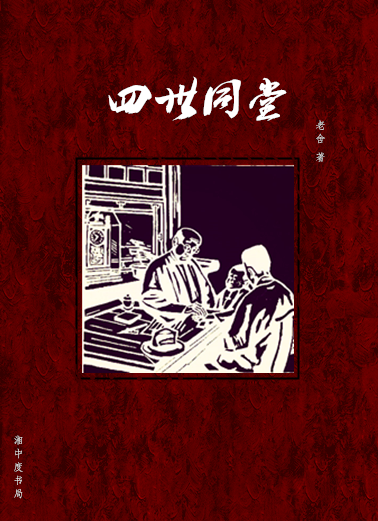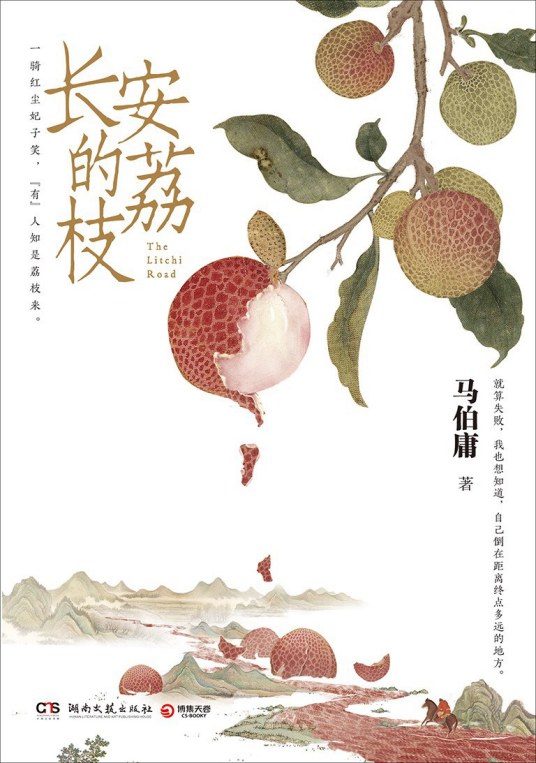《黄金时代》读后感1500字
叔本华说:人在四十岁以前,过得很慢,过了四十岁,过得就快了。
我不知道这位大哲学家为什么将分水岭定为40岁,当然,你可以定为45岁,50岁。过了这个岭,你就对发生的事见怪不怪了,对没有发生的事,不再充满期待了;过了这个岭,我们开始热衷回忆了,回忆那些似水流年,回忆那些金色年华。
第一次的理想,第一次的恋爱,第一次的“性”福,第一份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第一次当领导……你可能总是后悔在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年岁里,少了几个“第一次”;在时代大潮的风浪里,我们每个渺小的个体,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时、那些景,构成了我们的金色年华。
一个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小伙,初中二年级开始早恋,向女同学“线条”展示自己异“长”的阳物;17岁被下放到云南边陲放牛种地,在与少数民族相处中,接受劳动改造与阶级斗争的洗礼。在青春勃发的季节,在贫瘠闷热的雨林里,他与一个被称为“破鞋”的离婚女医生“陈清扬”,忘情地研究男女的生理构造,将自己的处男之身献给了科学又矜持、坚决要求戴套的女人。他们逃离军垦农场的监视,准备逃往缅甸,在边境的山坡上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文化革命要结束时,这个被称为“王二”的北京小伙,又被下放到京郊插队,在那里他偷偷地读书、写诗。他独特的诗才,吸引了年轻的北京文艺青年“小转玲”,他们恋爱,他们背着父母同居。等王二接受贫下中农改造结束,他考上大学,毕业分配到“矿业学院”任教;他的不羁与放荡,他的特立独行,他的诗人气质,成了这所大学的反面典型与奇葩人物;他研制出炸药,为此坐过牢;他目睹过大字报满天飞的场景下,一些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是如何被殴打致残、跳楼身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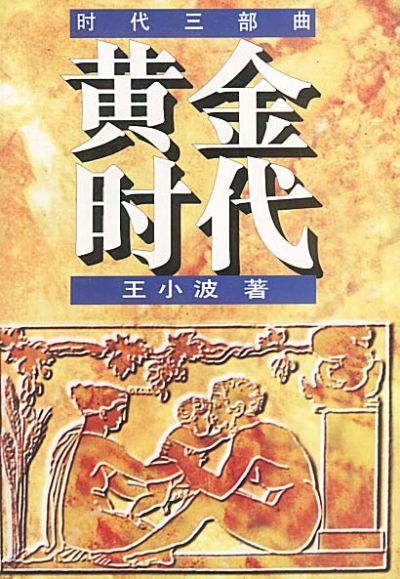
四十岁之前,主人公王二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在动荡的政治风云中,过着不平凡的日子:那是激烈的,那是贫困的—激烈到每天都斗志昂扬,揪出所有人性善与恶对立面中的矛盾,因为那时讲“阶级斗争”为纲;那是贫困的,贫穷到吃不饱、穿不暖,年轻人只好疯狂地做爱来消磨时光与慰藉生命。
但是这样的岁月,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值得浓墨重彩的;因为那时的我们充满欲望,充满好奇,精力无限---所以,正如这本书的名字一样,被王二称为“黄金时代”。
在云南边疆,有一种公牛,为了让它安心耕地,防止滥情,都要进行阉割。对一般的公牛,只用刀割去即可;但对于格外生性者,就必须采取锤骟术,也就是割开阴囊,掏出睾丸,一木锤砸个稀烂。从此后,受术者只知道吃草干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连杀时都不用捆……当我们男人过了中年后,想起这个情形,你可能会觉得,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越是这样,我们越是怀念各自的“金色年华”:那时心仪的姑娘,我为什么没有大胆地牵她的手,走过一段年老后值得回忆的路?那时的书本,我为什么没有多读几页,可以有才华将以后的日子写成诗、编成小说?那时的朋友,我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珍重,年老时我们吹起牛来有更多佐料?
岁月如流,就如月在当空,照着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这是过来者的生命感悟,也是生活客观规律的揭示。
作者王小波是一个率真而直言的自由主义者,他的作品早期都是在海外才得以出版;他没有刻意地歌功颂德,或者对政治事件评头论足,没有肩负起对读者说教的责任,因为他信奉夫子的话:“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他写人性深处的骚动,他写人性本来的情与欲,他写个体在时代大幕下的倾扎,他写向阳而生与落花无奈….我觉得,他的作品是可以跨越国界、赛过时间的。
王小波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多少有些苦涩与悲戚;对这个时代的记述,被后人称之谓“伤痕文学”~~那是中国那个特殊年代的伤痕;但对每个人来说,对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讲,那是有滋有味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