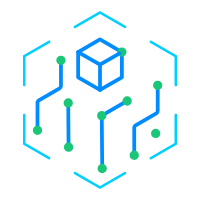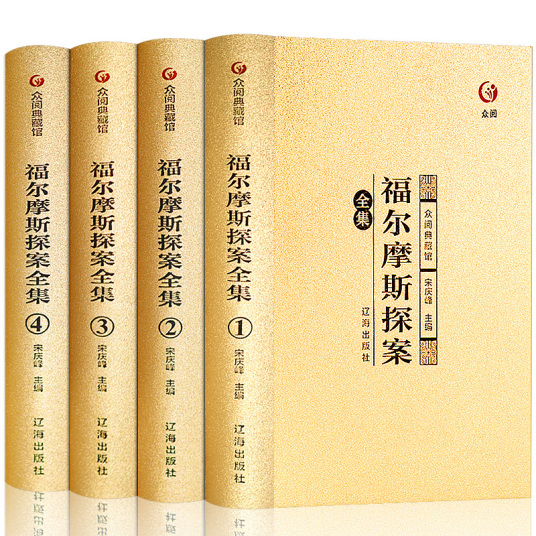日瓦戈医生读后感4000字
《日瓦戈医生》在我书柜的最高一层静静躺了好一段时日了,之所以一直没翻动它,一是枕边书太多顾不过来,二是对俄国小说里动不动一长串的复杂人名总觉得心有余悸,生怕把脑子烧坏也理不出人物关系来。但是GX对我说,你既然封在家里无事可做还容易抑郁,你总要做点啥解闷吧,看看书,看看电影,再写一写这个,你看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呢?我只有踩在凳子上取下书来,老老实实埋头啃呗。
《日瓦格医生》时代背景恢宏壮阔,时间跨度从1903年写到二战,人物历经一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二战,当之无愧的史诗级作品。以我的肤浅水平,如果想从宏大叙事角度去展开剖析,我既把握不住时代脉络,也做不到深刻剖析说理,最后大概率会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那我还是从女性视角,从个体生命在时代巨变中的情感体验的角度去观察、分析并稍加思考吧。Okay,那就重点从尤里(日瓦戈医生的昵称)和拉拉、冬妮亚的三角恋情来展开吧。这个角度毕竟庸俗,但我还是尽我所能让这个媚俗角度的评述变得稍微不那么的俗气吧。
尤里是一名医生,但更是一名诗人。整部作品之所以在恢宏的历史长卷中展开情节,却又能无时无刻不透出一种诗性的优美、典雅,这和作品中大量的篇幅是以尤里的视角来观察息息相关。尤里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文化、艺术的熏陶深入骨髓。尽管父亲在挥霍光家里的万贯家财后跳火车自杀身亡,母亲又因疾病过早离世,但尤里受哲学家舅舅的影响,一直对哲学、诗歌情有独钟。
尤里后来被舅舅寄养在冬尼娅家,和冬妮亚青梅竹马长大。用冬妮亚母亲的话说,他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尤里也认为上天注定冬妮亚就是他的妻子。在最适合谈婚论嫁的年龄,他们自然而然地结为夫妻,没有丝毫勉强的地方。无论他们自己看来,还是外人看来,他们就是理所当然应该在一起的。影片中,冬妮娅身着一身毛绒绒的粉红色裙装欢快地跳下火车,她天真活泼、纯洁无瑕,给人一种阳光明媚的感觉。当她和早已等候在车站的尤里深情相拥时,谁不认为这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
与冬妮娅的单纯截然不同的是,拉拉的性格就显出了多个层面的复杂性。毕竟,每个人的人生展开的背景和方式各式各样,附加在每个人身上的性格和命运也就截然不同。拉拉自幼丧父,软弱的母亲带着拉拉和弟弟,跟随贪财好色的律师科马罗夫斯基来到俄罗斯。母女两人都先后沦为他的情人。拉拉在情窦初开的年龄,也有从小一起长大并互相爱慕的恋人帕沙(后来成为拉拉丈夫),但恶棍科马罗夫斯基却在拉拉十六岁时给她上了有关情欲的第一课。这让拉拉既体验到初尝禁果的迷醉感,又因此陷入蒙羞受辱的极度痛苦之中。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圣诞节,拉拉悄悄潜入圣诞舞会,勇敢地向科马罗夫斯基开枪。科马罗夫斯基只受到皮外伤,但他因迷恋拉拉,还是想办法帮拉拉逃脱了警察的追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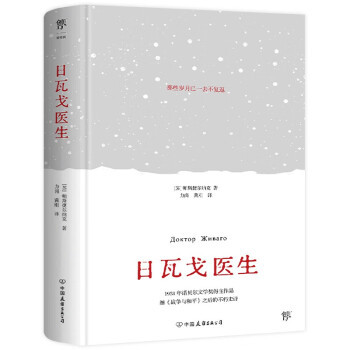
正因为有这样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拉拉过早告别了少女的天真单纯。拉拉无疑是美丽的,但她美丽的底色中有无限隐忧,她聪明好学上进,她希望通过不断提升自己掩盖无情命运强加于她的瑕疵,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配得上帕沙的纯粹的爱。她对帕沙没有欺骗隐瞒,帕沙仍然深爱着她,因为爱,两人克服内心的伤痕仍然坚持走到了一起。但阴影和裂痕在这对恋人的关系中却从此悄然埋下了。尽管两人都尽可能小心翼翼不去触碰它,但伤痕一直在那里,从未远去。
正直、勇敢的帕沙发誓要改变这一切,改变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秩序,消灭这个人剥削人的罪恶制度,让千千万万和拉拉一样的女孩不再受到侮辱和伤害,他离开拉拉母女报名参军,在一战中帕沙成了一名陆军中尉,十月革命之后成为了手握生杀大权的红军作战司令。在他实现社会理想的过程中,他离拉拉反而越来越远,他的大脑也日益被诸多抽象的概念填满,因而也使自己越来越远离具象化的个人,他越来越成为一种标志,一种符号,一种主义的象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个体属性却日益被抽离。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成为军医的尤里和成为护士的拉拉相遇。尤里是认识拉拉的,在拉拉母亲企图服毒自杀的那个夜晚,尤里看到了那个美丽的、受惊吓的拉拉。这是个和自己的妻子冬妮亚性格截然不同的女性。在战火硝烟中,她坚强、沉着,努力适应恶劣的战争环境,与医生尤里在工作中配合默契。他们实在是太相配了,以至于同事都忍不住说他们天生就应该在一起。但,尽管互有好感,此时理性的他们并没有逾越那道防线。正因为此,尤里在给冬妮亚的信中才会光明正大地提到拉拉,并夸赞她的美好。
但是敏感的冬妮亚却感觉到了。都说女人的直觉是最准的,果然啊。尤里在写信时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已悄悄爱上了拉拉,如果他已经意识到,信的内容可能完全不一样。拉拉是如此的美好,以至于尤里情不自禁地、毫不掩饰地想要向家人抒发对她由衷的赞美,而忽略了冬妮亚作为一个女人,是完全可以从中察觉出点什么来的,拉拉的气场真是强大无敌啊。亲爱的读者、观众,在此你可以批评尤里的傻气,毫无经验,但其实陷入恋爱而不自知的人,对这些事,自己是完全察觉不出来的。我想起了一首日语歌《迷路的天使》中的歌词:“若陷入恋爱,就会吹起喧嚣的风。迷路的天使,在我身边慌慌张张......”在尤里的眼中,拉拉就是这样的天使吧。
战争结束,尤里和拉拉分别,尤里回莫斯科和家人团聚,拉拉则继续去寻找失踪的丈夫。回到莫斯科的家中,尤里才发现自家的大房子已经挤满了不相干的陌生人,十月革命之后,穷人都翻身了,在供给制之下,像自己这样的资产阶级家庭,多余的私有财产是需要拿出来平均分配的。尤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内心本来就主张平等,同情弱者,对财产的丧失并不以为意。但作为诗人内心敏感的他,还是感受到了真切的痛苦。原有的秩序崩坏了,自己弥足珍视的个人情感、个体价值这种东西,被新时代视为资产阶级的残余,是需要像切割毒瘤一样予以抛弃的,因此在当下竟是如此与社会中的其他人格格不入。新的社会价值不需要个体意识,诗歌之类关注人类心灵、彰显个体生命价值的东西注定与宏大叙事相去甚远。尤里这个骨子里的诗人,这个柔弱的百无一用的书生,在他人眼里,注定成为危险人物。因为,简单地说,他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而新社会要求的是整齐划一,消除一切个人色彩,融入集体中,并保持高度共性,也就是说连眼神都不应当具备个性,我突然想起了小说中有一处提及帕沙空洞的眼神心中不禁一震。而尤里的诗人和哲学家气质让他无论行走在哪里,都那么显眼,莫斯科不仅仅是物品匮乏住不下去了,他不愿丧失自我的高傲的眼神也常常出卖自己,让一切充满危险。他就是一个无法融于新时代的顽固保持旧时代精神的危险人物,尽管他手无寸铁。于是,一家四口仓皇逃离了莫斯科,一路历经艰辛,颠沛流离,来到了乡下老家瓦雷金洛。
作者安排尤里和拉拉在瓦雷金洛的图书馆再次邂逅。这次他们不再理性、矜持、克制,久别的重逢点燃二人长久压抑的激情,如同经冬的积雪一到春天自然而然地消融,如同含苞的花朵在阳光下自然而然地绽放,他们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了。拉拉的强大魅力让失去理智的尤里一有机会就骑马前往奔赴拉拉。爱情甜蜜而痛苦,尤里的心极度矛盾而无法自拔。毕竟冬妮亚作为妻子的表现也达到了几近完美的程度。在尤里一次前往会见拉拉的路上,尤里被游击队俘获,再次被迫与家人分离,与拉拉分离。在游击队的日子里,尤里再次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也目睹了人性的极度分裂和沦丧。他终于忍无可忍,想方设法逃离了游击队的掌控,回瓦雷金洛去见他日夜牵挂的家人。但家人已经去了莫斯科,落魄的尤里和拉拉再次相聚,他和拉拉在一起共度了短暂而又最美好的时光,在窗外白雪皑皑、严寒的冬夜,远处有群狼的哀嚎,在这样的一个个夜晚,在极度恶劣、危险的自然环境中,身边有着爱人的陪伴,尤里诗意盎然,思如泉涌,为拉拉写下了不少动人的诗篇。
由此我不免感叹,无论环境多么恶劣,精神世界的充实,灵魂的契合,可以让一个人在多大程度抵御那些随时可能摧毁自己的外部力量,作为一个柔弱的知识分子,尤里体弱多病,但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他依然坚守内心的道德律和审美标准,努力让自己不被时代同化、吞噬。我又想到,为何尤里和拉拉会如此相爱,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拉拉外在的美丽,更多的还是在于他们彼此价值观的高度契合带来的心灵的融为一体。他们同属内心最不容易被外界改变、最不容易被驯服的一种人。他们的内心属于同种质地。拉拉提到,他依然深爱着帕沙,但是他们婚姻中确有一种东西被损坏掉了,如果帕沙不是非要去追求那些宏大的革命理想,没有变成那个在世人眼里无比权威、无比高大上却又因而高度符号化的、眼神空洞的人的话。
因此,我觉得吧,拉拉不再爱帕沙相对容易理解,毕竟帕沙早已丧失了很多作为具体、感性的独立存在的个体的基本特征。而尤里对拉拉,对冬妮亚,我认为应该是同时都深爱着的。只是爱的性质不一样。冬妮亚简单而美好,拉拉内心强大,充满无比的力量。正如冬妮亚所说,冬妮亚总是力求简单,而拉拉则总是把事情搞复杂。这话说得真对。拉拉的性格就像璀璨的钻石在阳光下每一个棱角每一个侧面都折射出耀眼的光芒。这样丰富、立体的性格对一个喜欢探索世界的大宇宙和心灵的小宇宙的诗人尤里来说,当然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必然会深陷其中并值得用痛苦的余生去追忆拉拉的美好。
毕竟人是非常复杂的高等生物。在我看来,理论上一个人是完全有可能也有能力爱上个性迥异的不同的人的。人生际遇各有不同。有的人庸庸碌碌因而刚好安然地度过一生,无惊无险,没有机会遇到那个令自己怦然心动的另一人,或者说,很多人一生中连一次真正的恋爱也不一定遇到,遑论两次,自然不会面临是否忠于婚姻的考验并陷于自我折磨之中。而另有一些人,他们感知世界万事万物的能力比普通人强,因而更有天赋,无论历经多少苦难,内心依然完好无损。哪怕时光不断逝去,他人早已被生活折磨得麻木不仁的时候,他(她)的心灵依然能敏感、细腻地感知世间美好,再次邂逅爱情的可能性自然比普通人大。不能再写下去了,再写一定会有无数卫道士跳出来指责我为婚外恋辩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