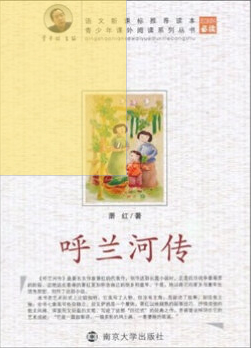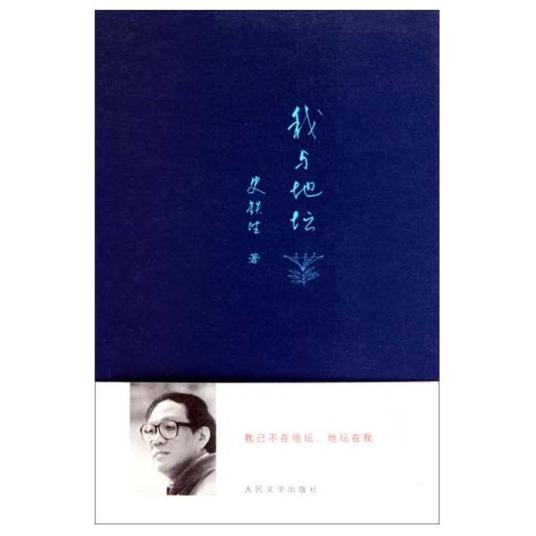莫言蛙读后感2000字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在莫言的作品《蛙》中,在他展示的那个胆大妄为、敦风厉俗、爱憎分明的世界里,在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里,涌动着悲悯之心,大义之情。
小说以姑姑万心为主角,以她用倔强和铁面无私推动着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落地、落实的故事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人的伟大与卑微、忠诚与忏悔。姑姑是一个根正苗红的乡村妇科医生,有高超的接生技术,在1953年4月4日至1957年12月31日期间,她接生了1612次,接生了1645名婴儿。在那些妇女眼里,她是活菩萨,是送子娘娘,是妇科圣手。那些年,是她的黄金时代。
这些光辉,在1965年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那一年开始,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村民们咒骂、反抗。作为一个妇科医生,原本最爱听初生婴儿的哭声,但是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党的忠诚者,不得不残忍,美妙的婴儿啼哭声,成了千千万万母亲的哀乐。她未婚未育,在为一个个怀二胎的母亲做流产手术时,被责骂过,被诅咒过,被殴打到头破血流过,内心似乎毫无波澜。却在晚年婚后,用让丈夫捏泥娃娃的方式,创造了2800个泥娃娃,那是她曾经扼杀的生命,姑姑在想象里为他们规划了一场新的人生。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她是伟大推动者中的一员,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与落后经济之间的矛盾需要去解决。在人伦道德为上的乡村环境中,她卑微而倔强。计划生育是一面镜子,照射出了时代任务的沉重与悲悯情怀的底色。

小说写的看似是她一个人,实则是一群人。她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医学技术专业人员,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她面对的是一群时代使命意识朦胧、生命意识日渐强烈的村民。那些偷偷怀二胎的人只知道:“只要孩子出了‘锅门’,就是一条生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就会受到保护,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孩子是祖国的未来。”生育繁衍,庄严而世俗。朴素的劳动人民都在期盼着生育,庆贺着生育,歌颂着生育。政策的落地、国家的发展需要控制生育。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个人所承受的压力和困难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在个人的生活中却产生巨大的影响。姑姑活在职业道德与时代任务的对抗统一之中,如履薄冰又坚定无比。人人都说她无情、心肠硬,最后她和助手小狮子撑着竹筏追赶七个月身孕身高却不足一米的王胆时,看到王胆在拼尽全力地用力,发出令人毛骨悚然、撕肝裂胆的哭叫声,姑姑伸出她的手,那双曾被村里人敬畏夸赞现如今被视为“魔爪”的手,为王胆接生,一声婴儿暗哑的哭声划过水面。水下流淌的,是她不曾失去的悲悯之心。
我曾经思索,计划生育政策除了促进人口增长与经济落后之间的平衡,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命题值得我们去探索、思考。以前听母亲讲过,那个年代每个家庭有七八个孩子是正常现象,多一个孩子家里便多一个劳动力,这是次要的,主要是为了生一个男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根深蒂固,男性被视为家族的继承者,被赋予了继承祖业家产、延续家族血脉的责任。所以当家庭的口粮无法养活这么多孩子的时候,若生下个女儿,大概率会选择将孩子送给别人,或遗弃在某个地方任其自生自灭,或者甚至直接溺死。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中写道:“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不管是传统封建观念,还是贫穷的民生现实,思想需要改变,意识需要觉醒,那些人性身上本该有的恭敬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需要一一唤醒。既然做不到从始至终尊重生命、守护生命,那么从一开始便不要怠慢生命。在某种程度上,计划生育也在告诉我们,对生命要怀有敬畏之心、悲悯之情。
莫言在最后给杉谷义人的信中提出了一个疑问:“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净呢?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这个问题触及千千万万中国人生命与灵魂之痛处。一段历史是由一代人共同书写的,时代的任务并不是一个人去承担,结果也不应由一个人去承受。中国的计划生育面对的问题复杂,它涉及政治、经济、人伦、道德、传统观念,无法以简单的爱与恨、对与错、成功与失败去加以评判,时代的发展终会给出答案。怜悯和理解是解锁心灵深处的两把钥匙,像姑姑这样伟大而卑微的忠诚者,终会得到包容、谅解、敬重。
海涅说:“悲悯之心是一艘穿越人生起伏的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困境、理想困境,但中国人的生命韧性和悲悯情怀总能将苦难一一化解,用悲悯之心在自我和他人之间架设一条桥梁,实现共进。在时代浪潮中,满怀悲悯之心,渡他人,渡自己,凝聚人间的温暖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