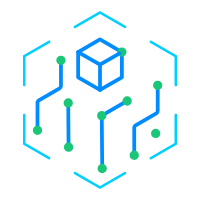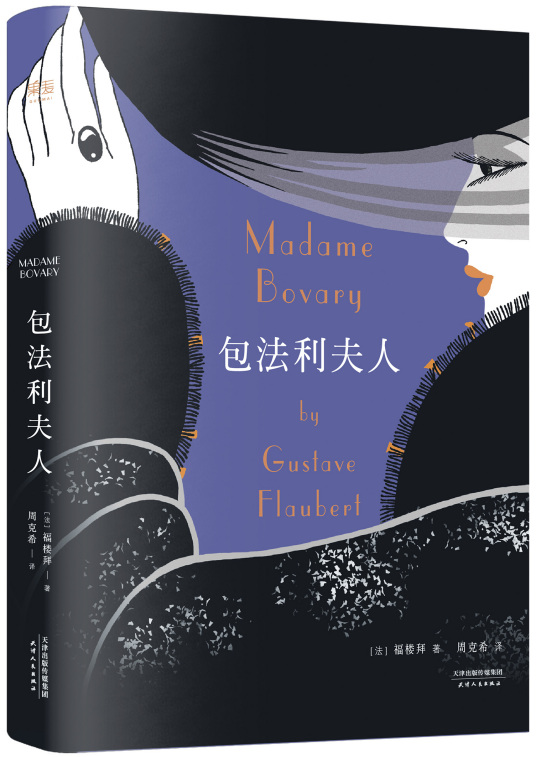我与地坛读书笔记1200字
翻开《我与地坛》的那一刻,我仿佛被带入了一个由石头、树木与轮椅轨迹构成的宇宙。史铁生以他特有的平静而深邃的笔触,勾勒出的不仅是北京城里一片普通的园林,更是一个灵魂在绝望边缘寻找栖息地的精神图景。这本书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每个现代人内心深处关于存在意义的追问。
史铁生的文字有一种奇特的质感——既坚硬如地坛的石碑,又柔软如初春的新芽。他在轮椅上度过的那些漫长岁月,似乎没有让他变得愤世嫉俗,反而赋予了他一种穿透表象的洞察力。当他写道“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残疾作家在自怜自艾,而是一个灵魂在宇宙的宏大叙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地坛对史铁生而言,早已超越了物理空间的范畴。它既是他的避难所,也是他的疗愈室,更是他与命运对话的祭坛。在这片被时间浸染的土地上,每一个季节的更迭、每一片落叶的飘零、每一只虫蚁的爬行,都被赋予了哲学的重量。这让我想起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描述的那个不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在看似无意义的重复劳动中,史铁生在地坛的徘徊同样找到了一种对抗虚无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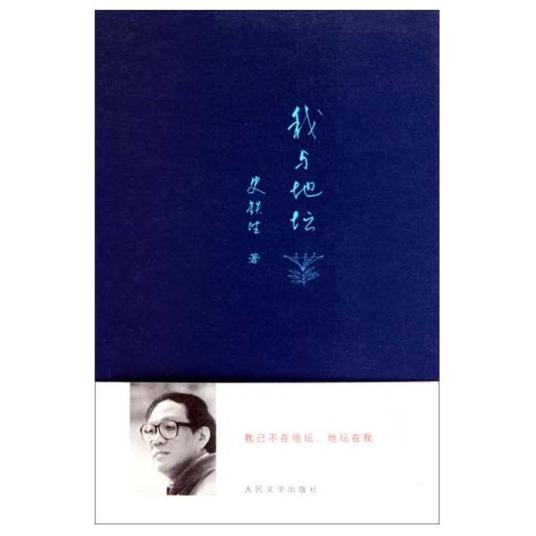
最触动我的是史铁生对母亲的回忆。那些克制而深情的文字背后,是一个儿子迟来的理解与无法弥补的愧疚。当母亲悄然跟随他去地坛,又因怕打扰而悄然离去;当母亲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背后隐藏的却是无数个担忧的日夜。这种爱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渗透在日常细节中的沉默守护。在个人主义日益膨胀的当下,这种克制的亲情书写提醒我们,生命的意义往往不在远方的星辰大海,而在近处那些被我们忽视的温柔目光中。
史铁生对残疾与健全、短暂与永恒的思考尤其深刻。他拒绝将残疾浪漫化,也不将其妖魔化,而是以一种几乎科学的冷静态度剖析这种状态如何重塑了他的存在体验。“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他写道,“我想走而不能走,健全人想飞而不能飞。”这种对“局限”的普遍性的洞察,消解了健全与残疾的二元对立,将所有人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我们都在各自的局限中寻找突破的可能。
《我与地坛》出版于1990年代,那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在物质主义开始萌芽、价值观剧烈震荡的年代,史铁生却将目光投向内心与永恒。这种内转不是逃避,而是一种精神的锚定。当外部世界变幻莫测时,他在地坛找到了某种恒常——不是不变的恒常,而是变化本身的恒常,是四季轮回、生死交替中蕴含的生命韵律。
阅读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想到:如果是我,遭遇如此重创,是否还能保有这份凝视深渊的勇气?是否还能在绝望的土壤中培育出希望的幼苗?史铁生没有给出廉价的答案,他只是在文字中展示了一种可能性——当身体被困于轮椅,心灵却可以在地坛的广阔时空中自由漫步。
《我与地坛》最终是一本关于接纳的书。接纳不完美的身体,接纳无法重来的过去,接纳终将到来的死亡。但这种接纳不是被动的屈服,而是主动的拥抱——拥抱局限中的可能,拥抱短暂中的永恒,拥抱个体伤痛中的人类共通命运。
合上书本,地坛的影像却在我心中生了根。也许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地坛”——那个在生活风暴中可以退守的精神空间,那个可以重新校准生命坐标的参照点。在日益喧嚣的世界中,史铁生借地坛发出的声音依然清晰: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逃避痛苦,而在于如何带着痛苦继续前行;不在于追求永恒的幸福,而在于在有限中发现无限。
那片古老的园林,因一个人的沉思而获得了全新的生命;而这个人的生命,也因一片园林的庇护而得以在绝望的边界开出最坚韧的花。这就是《我与地坛》给予我们的最好礼物——不是答案,而是一种在黑暗中依然保持凝视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