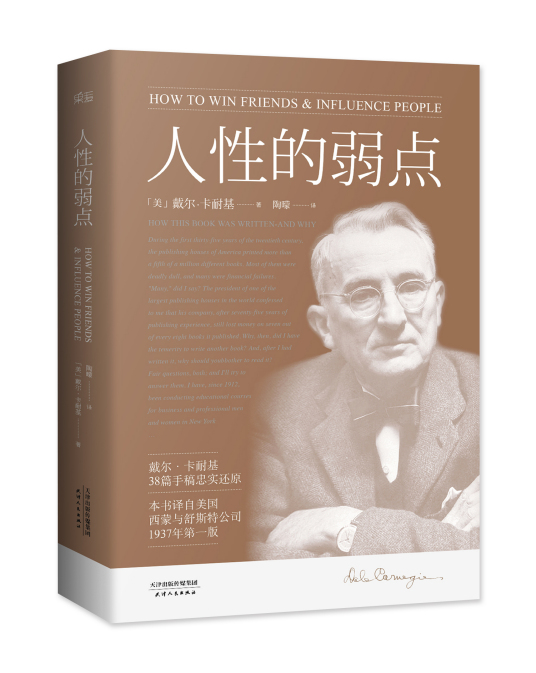空城纪读后感1000字
漫步在新疆的街道,“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标语随处可见。石榴,新疆最美的果实,原产于西亚地区,于西汉时期通过张骞出使西域引入长安。出生于新疆昌吉的邱华栋用三十个短篇紧密嵌于六个中篇“子房”之中,最终聚合成一个完整的“石榴”——《空城纪》。
翻开邱华栋的《空城纪》,龟兹、高昌、尼雅、楼兰、于阗、敦煌六座西域古城的风沙裹挟着两千年的故事扑面而来。听,废墟在说话,龟兹石窟的琵琶余音未散,楼兰古城的牛角号隐约可闻,弟史公主的独白、商队驼铃的叮当、一枚简牍的叹息,甚至一匹穿越千年的花斑马——它从岩画跃入李公麟的画卷,在北宋汴梁哀悼死去的伴侣后,终于疲倦地永驻画中:“等到你在这幅画里看到我的时候,我就会在你的目光里活过来。”

器物是历史的声带,在《龟兹双阕》中,那把汉武帝赐予细君公主的汉琵琶贯穿始终。这把满月形的乐器不仅是思乡的寄托,更成为文化交融的见证。当细君公主怀抱琵琶吟唱“吾家嫁我兮天一方”时,中原的音律与西域的筚篥、羯鼓碰撞出奇妙的和声。到了唐代,白明月与火玲珑在长安宫廷用这把琵琶演奏《霓裳羽衣曲》,龟兹乐调与中原宫商完美融合,成就了盛唐气象的艺术巅峰。而在当代,音乐家李刚在龟兹废墟中寻得琵琶残件,琴弦虽断,却在现代音乐厅里激发出跨越时空的回响。这种“物的叙事”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史料,而是通过器物的流转,将文明基因注入当代生活的血脉。
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同样承载着文明对话的密码。精绝国细眉公主冒死将蚕种藏于锦缎中带回西域,丝绸从此在西域生根发芽。这些织锦上的云气纹与汉字铭文,既是中原技艺的见证,也是西域工匠创新的结晶。当现代考古学家在尼雅废墟中发现这片织锦时,千年之前的丝路驼铃仿佛在耳畔响起,诉说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与共生。
历史的书写终究映照着当代的目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在此得到文学印证。张骞被匈奴扣押十三载仍矢志西行的故事,不仅是汉唐气象的彰显,更是对当代精神的叩问。邱华栋在每座古城故事的结尾,皆安排当代人物踏入废墟:赵刚在尼雅梦中接过汉朝公主的蚕种,王刚于楼兰沙尘中拾起那柄命定的牛角号。“赵刚”“王刚”“吴刚”这些名字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千千万万华夏子孙的身影——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皱褶的探询者。
六座古城的兴衰,本质上是一部文明存续的启示录。高昌古城从车师前国的边塞小城发展为丝路重镇,最终却因过度垦殖消失在黄沙中。这种文明的轮回警示我们:任何文明的存续都离不开对自然的敬畏与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当现代城市在追求发展时,是否还记得如何在钢筋水泥中保留文明的根系?空城非空,废墟之下,历史的脉搏从未停息。